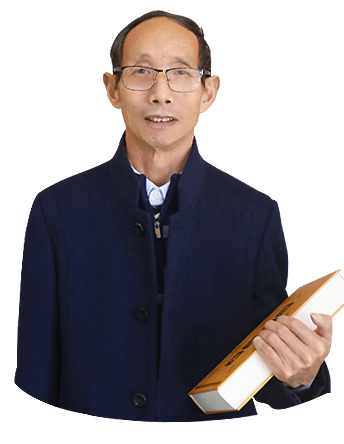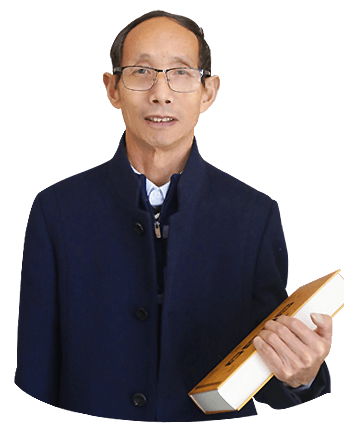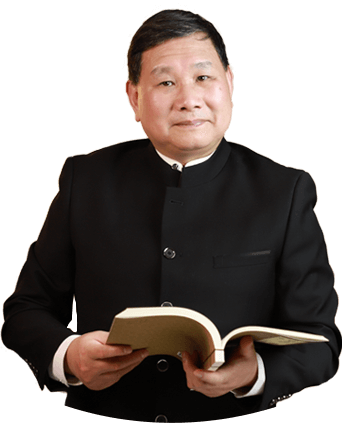菩萨蛮·忆郎还上层楼诗词取名
忆郎1还2上层3楼曲4。楼前5芳草6年7年绿8。绿9似去时10袍。回11头风12袖13飘。
4.楼曲:楼曲用作人名喻指接受能力快、身心愉悦之意。
5.楼前:楼前用作人名喻指前程似锦、乘风破浪、接受能力快之意。
6.芳草:芳草用作人名喻指推陈出新、花容月貌、赏心悦目之意。
7.年:年字含义为年华、青春、活泼、美好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举足轻重、福寿康宁之意;
8.年绿:年绿用作人名喻指如日方升、朝气蓬勃、财源广进之意。
9.绿:绿字含义为新生、活力、清新、神清气爽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朝气蓬勃、风华正茂之意;
10.时:时字含义为时彦、时候、光阴、时机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鸿运当头、顺水顺风之意;
11.回:回字含义为答复、环绕、回族、章节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一语中的、精妙绝伦之意;
12.头风:头风用作人名喻指出类拔萃、雷厉风行之意。
13.袖:袖字含义为领袖、衣袖、红袖、领袖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多才多艺、运筹帷幄之意;
郎1袍应已2旧。颜色3非长4久5。惜6恐镜中7春8。不如9花草10新11。
1.郎:郎字含义为男子、丈夫、年轻、风度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年轻俊朗、风度不凡之意;
2.应已:应已用作人名喻指慨然应允、彬彬有礼之意。
3.颜色:颜色用作人名喻指美艳绝伦、慈目善眉、花容月貌之意。
4.非长:非长用作人名喻指举足轻重、聪明绝顶、雄才大略之意。
5.久:久字含义为久久、久远、永久、时间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持之以恒、源远流长之意;
6.惜:惜字含义为怜惜、呵护、惜时如金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爱如珍宝、掌上明珠之意;
7.镜中:镜中用作人名喻指忠肝义胆、察言观色、细心慎重之意。
8.春:春字含义为春天、生机、生命力、春季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年轻活泼、朝气蓬勃之意;
9.不如:不如用作人名喻指天从人愿、气宇轩昂、出类拔萃之意。
10.花草:花草用作人名喻指推陈出新、楚楚动人之意。
11.新:新字含义为更新、新鲜、清新、新近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清新俊逸、青出于蓝之意;
译文及注释
译文
心中思念情郎,于是登上高楼远望。楼前的芳草,一年一绿,如今又是春天来到。这青翠的绿色仿佛情郎离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。分别时,他不忍离去,回首凝望,衣袖随风飘动。
一别数年,他崭新的衣袍恐怕已经变旧了吧。新绿的颜色也已经暗淡无光了吧。其实韶华易逝,就连镜中的容颜也一年一年地逐渐减色,不像芳草那样岁岁依旧。
注释
菩萨蛮:原为唐教坊曲名,后用为词牌名。亦作“菩萨鬘”,又名“子夜歌”“重叠金”等。
楼前芳草年年绿:此句化用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赋“王孙游兮不归,春草生兮萋萋”,及王维《山中送别》诗“春草明年绿,王孙归不归”。
镜中春:指镜中女子的容颜如春光般姣好。
赏析
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。起首“忆郎还上层楼曲”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,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。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,多从空间落想,怅望行人此去之远。第二句“楼前芳草年年绿”,则从时间落想,因见芳草“年年绿”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。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,它取意于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与王维《山中送别》句意,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。
三、四两句“绿似去时袍,回头风袖飘”,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“绿”字为桥梁,从“芳草年年绿”到“绿似去时袍”,由望景过渡到怀人,感今过渡到思昔。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,勾起回忆,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,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、回首相望时,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。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,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;此时,因望见芳草绿、想到“去时袍”,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。此时此事,此情此景,真是“中心藏之,何日忘之”(《诗经·小雅·隰桑》)。从这两句词,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,也可以想见其此时“忆郎”时的惆怅。牛希济《生查子》词中的“记得绿罗裙,处处怜芳草”可与这两句词参读,不同的是:张先词就居者立言;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。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,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。
换头“郎袍应已旧,颜色非长久”两句,紧承上片的三、四两句。词笔不离衣袍,而又翻出新意。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,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,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。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,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。同时,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“年年”两字遥相呼应,也是从时间落想,暗示别离之长久。正因别离已久,才会产生衣袍已旧、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。又从袍之旧、色之褪,触发青春难驻、朱颜易改之感。于是,自然引出下面“惜恐镜中春,不如花草新”两句,把词意再推进一步。词中人之所惋惜、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、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,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。离别固然折磨人,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,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;至于人生短促、岁月无情,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,这却是无可挽回、无可补偿的,正所谓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”(王国维《蝶恋花》)。这两句词,则对照眼前“芳草年年绿”之景,怨叹人之不如花草。花落了,明年还会开;草枯了,明年还会绿;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。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,不会岁岁更新。刘希夷诗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(《白头吟》)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。
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,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,并用以穿针引线,贯穿全篇。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,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,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,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,合为词境。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,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,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,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。上片因“忆郎”而“上层楼”,因“上层楼”而见“楼前芳草”,因芳草之“绿”而回忆郎袍之“绿”,再因去时之“袍”而想到风飘之“袖”。首句与次句的两个“楼”字,紧相扣合;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“绿”字,上下钩连;第四句的“袖”字固与第三句的“袍”字相应,句中的“回头”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“去时”两字相承,针线绵密,过渡无痕。下片虽另起新意,却与上片藕断丝连。因三、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,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;过片两句的上、下句间,则是因衣袍之“旧”而致慨于“颜色非长久”。接下来的两句,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“镜中春”也不长久,再回溯上片“芳草年年绿”句,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。通篇脉络井然,层次分明。

 张先
张先
 陈师道
陈师道 高适
高适 列子
列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