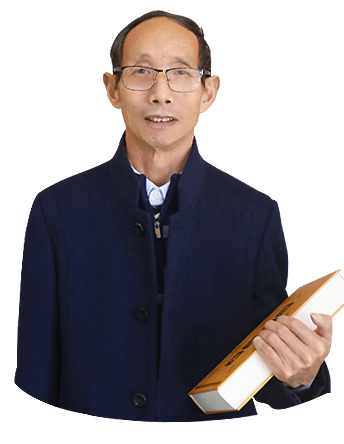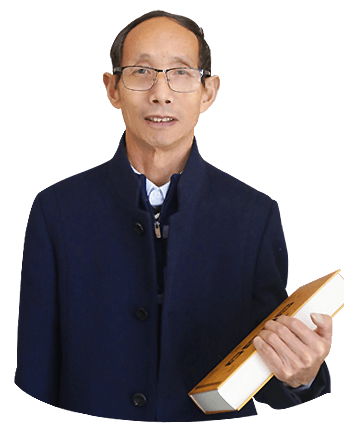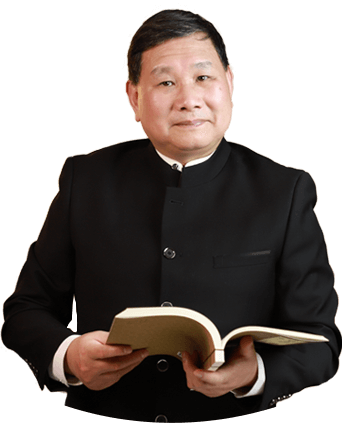咏三良诗词取名
束1带值2明后3,顾盼4流辉5光6。
4.顾盼:顾盼用作人名喻指善解人意之意。
5.流辉:流辉用作人名喻指光辉灿烂、魅力四射之意。
6.光:光字含义为明亮、照耀、光彩、荣耀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功勋卓著、朝气蓬勃之意;
一心1在陈2力3,鼎列4夸四方5。
1.一心:一心用作人名喻指善始善终、专心致志之意。
2.在陈:在陈用作人名喻指冰雪聪明、循循善诱之意。
3.力:力字含义为活力、力气、能力、动力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意气风发、干劲十足之意;
4.鼎列:鼎列用作人名喻指顶天立地、成熟稳重之意。
5.四方:四方用作人名喻指才德兼备、心怀大志、高瞻远瞩之意。
款1款效忠2信3,恩义4皎如5霜6。
1.款:款字含义为款心、真诚、诚恳、钱财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赤诚相待、家财万贯之意;
2.效忠:效忠用作人名喻指尽职尽责、碧血丹心、事半功倍之意。
3.信:信字含义为诚实、信然、诚信、果真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信以为本、一诺千金之意;
4.恩义:恩义用作人名喻指感恩之心、饮水思源之意。
5.皎如:皎如用作人名喻指顶天立地、天从人愿、心思澄明之意。
6.霜:霜字含义为霜操、高洁、霜法、冷酷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高风亮节、不染纤尘之意;
生时1亮同2体3,死没宁分4张5。
1.生时:生时用作人名喻指鸿运当头、生生不息、财源广进之意。
2.亮同:亮同用作人名喻指交口称赞、魅力四射、刚正不阿之意。
3.体:体字含义为身体、体育、体能、形体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善解人意、心胸宽广之意;
4.宁分:宁分用作人名喻指明辨是非、平安喜乐、宁静致远之意。
5.张:张字含义为增强、扩广、一弛一张、宽严相济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张弛有度、有松有紧之意;
壮1躯闭幽2隧,猛志3填4黄肠。
1.壮:壮字含义为勇气、强盛、豪杰、抱负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年轻力壮、豪情壮志之意;
2.幽:幽字含义为幽丽、幽静、幽美、幽趣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澄心清神、安之若素之意;
3.猛志:猛志用作人名喻指雄心壮志、大义凛然、势如破竹之意。
4.填:填字含义为填补、填满、补满、安定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饱读诗书、吉祥安乐之意;
殉死礼1所非2,况3乃用4其良5。
1.礼:礼字含义为诗礼、礼花、礼仪、礼貌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善气迎人、温柔敦厚之意;
2.非:非字含义为非同反响、非凡、与众不同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聪明绝顶、品貌不凡之意;
3.况:况字含义为更加、况荣、况复、赐予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冰清玉洁、超凡脱俗之意;
4.乃用:乃用用作人名喻指宽容大度、博学多才、文静内秀之意。
5.其良:其良用作人名喻指温柔敦厚、才德兼备之意。
霸基1弊不振2,晋楚3更张4皇5。
1.霸基:霸基用作人名喻指中流砥柱、脚踏实地之意。
2.不振:不振用作人名喻指卓尔不群、气宇轩昂之意。
3.晋楚:晋楚用作人名喻指楚楚动人、乐观进取、积极向上之意。
4.更张:更张用作人名喻指劳逸结合、张弛有度之意。
5.皇:皇字含义为皇上、高贵、敬称、闲适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独领风骚、举世无双之意;
疾病命1固乱,魏氏2言有3章4。
1.命:命字含义为生命、奉命、拼命、好命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自强自立、雷厉风行之意;
2.魏氏:魏氏用作人名喻指气慨豪迈、功成名就之意。
3.言有:言有用作人名喻指远见卓识、鼎鼎有名、聪明伶俐之意。
4.章:章字含义为文采、显著、花纹、规程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文采斐然、正直不阿之意;
从1邪陷厥父,吾2欲讨彼狂。
1.从:从字含义为乖巧、聪明、顺从、依从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行成于思、温顺乖巧之意;
2.吾:吾字含义为吾侪、吾爱、预防、无畏等之义,用作名字寓意为坚若磐石、固若金汤之意;
创作背景
这首诗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(809年)贬谪永州(今属湖南)期间读书有感而作。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(805年)被贬来永州,而唐宪宗即位(806年)后,仍信谗贬贤,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,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、迷茫和郁愤。
译文及注释
译文
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,他们才高志大,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。
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,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,受到四方称颂。
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,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。
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,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。
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,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。
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,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!
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,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。
魏武子之所以不从父命,以人为殉,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,遗命不需要遵从。
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,陷入父皇陷阱,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。
注释
秦穆公卒,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,皆秦之良也。
明后:明君,谓秦穆公。
幽隧:墓道。
黄肠:苏林曰: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,故曰黄肠,指棺木。
张皇:张大、扩大。
从邪:指殉葬之作法。
彼狂:指秦穆公子康公。
赏析
“三良”事最早见于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。据《左传》鲁文公六年载,“秦穆公任好卒,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,皆秦之良也。国人哀之,为之赋《黄鸟》。”此后史家、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,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,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,三良自愿殉葬;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、个体生命价值的,如陶渊明、苏轼等等。
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。前十句为第一层,是就三良来说。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,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、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。应该说,这与《黄鸟》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。《黄鸟》首章云:“交交黄鸟,止于棘。谁从穆公,子车、奄息。维此奄息,百夫之特。临其穴,惴惴其栗。彼苍者天,歼我良人。如可赎兮,人百其身”。清马瑞辰曰:“诗以黄鸟之止棘、止桑、止楚,为不得其所,兴三良之从死,为不得其死也。棘、楚皆小木,桑亦非黄鸟所宜止,《小雅·黄鸟》诗‘无集于桑’是其证也。”马说甚是。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“临其穴,惴惴其栗”,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,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。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,也是有所本的。汉末王粲《咏史诗》论三良之死曰:“结发事明君,受恩良不訾。临末要之死,焉得不相随?……人生各有志,终不为此移。同知埋身剧,心亦有所施。”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。二诗对照,无论是“束带值明后”与“结发事明君”的细节描绘,还是“生时亮同体,死没宁分张”与“人生各有志,终不为此移”的死亡价值判断,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。究其原因,王粲《咏史诗》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,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,故宣扬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精神,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。而柳宗元《咏三良》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,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,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。其《读书》一诗云:“幽沈谢世事,俛默窥唐虞。上下观古今,起伏千万途。遇欣或自笑,感戚亦以吁。”《咏史》之咏叹燕昭王、乐毅,《咏三良》之批判秦康公,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。其《冉溪》诗云:“少时陈力希公侯,许国不复为身谋。”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,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,使得“人情大悦”,政局为之一新。“生时亮同体,死没宁分张”,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。
然而若撇开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的政治隐喻不谈,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,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。陶诗虽亦有“出则陪文舆,入必侍丹帷。箴规向已从,计议初无亏”的描述,但“忠情谬获露,遂为君所私”与“厚恩固难忘,君命安可违”的议论,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。事君以忠,为君所赏,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,但若过于忠诚,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,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。渊明说“忠情谬获露”,“谬”字真是深可玩味: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,“君命安可违”实乃“君命不可违”。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。人才乃国之公器,非国君的一己之私,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这直接启发了苏轼《和〈咏三良〉》“我岂犬马哉?从君求盖帷”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“杀身固有道,大节要不亏”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。宗元《咏三良》诗在这一点上,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。
《咏三良》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,是就秦康公来说。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,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,朱熹即云:“史记秦武公卒,初以人从死,死者六十六人。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,而三良与焉。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,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。于是习以为常,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。”在中原地区人看来,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,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,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。穆公死后,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,晋、楚相继称霸,这和穆公以贤殉葬、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。《左传》中“君子”即言:“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,死而弃民。先王违世,犹诒之法,而况夺之善人乎?……今纵无法以遗后嗣,而又收其良以死,难以在上矣。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。”宗元所论正是本此。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,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,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。《左传》鲁宣公十五年记载:“魏武子有嬖妾,无子。武子疾,命颗曰:‘必嫁是。’疾病则曰:‘必以为殉。’及卒,颗嫁之,曰:‘疾病则乱,吾从其治也。’”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。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,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。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,却没有康公的声音,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,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,康公命令他们不死,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,而且还可赢得人心,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,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。在这种情况下,康公如果选择沉默,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。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。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,然而倘若仔细研究,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。
首先,如前朱熹所言,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,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,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,没有与时俱进。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,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。
其次,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: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,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,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,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,在“父没,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的春秋时期,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,无可厚非。当然,康公以三良殉葬,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,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(他本可以挽救的),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,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。不过宗元说“吾欲讨彼狂”,称康公为狂乱之人,大加讨伐,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。苏辙以为:“然三良之死,穆公之命也。康公从其言而不改,其亦异于魏颗矣。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。”与宗元一样,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,自然也谈不上“了解之同情”了。
再次,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,如前所述,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。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“从邪陷厥父”。这里,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。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,康公如果改变父命,这无疑是正确之举。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,就诗歌本身来说,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,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,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,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。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。
猜您喜欢
蝶恋花·伫倚危楼风细细
拟把疏狂图一醉,对酒当歌,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

 柳宗元
柳宗元
 柳永
柳永 王十朋
王十朋 殷尧藩
殷尧藩